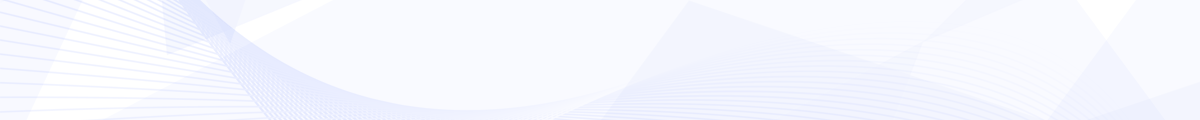下放地方立法权后,立法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的格局得到改变,地方立法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地方普遍有立法的激情和冲动。但在地方立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不抵触”原则下,在严格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下,在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上,存在着“看齐”与“特殊”的对立张力,存在着“法制统一”与因地制宜的矛盾困境。地方立法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如何释放地方立法的活力,如何立出管用之法,成了个大问题。
一、“地方性事务”模糊
“地方性事务”是联邦制下的一个特指概念,它与“中央事务”相对应。在联邦制国家,一般通过宪法来划分“中央事务”与“地方性事务”,因此“地方性事务”与“中央事务”是作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前提。
单一制国家,在宪法文本中并无“地方性事务”与“中央事务”划分之规定,中央和地方没有分权空间,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存在大量的交叉重叠之处,几乎找不出何为“地方性事务”,在立法事项上也根本不存在只能由地方立法而不能由中央立法的情形。
《立法法》第72条、第73条虽然罗列了地方性事权,但“地方事务”到底是什么?有多大?是不清晰的,立法法对于“地方性事务”的范围,采取的是“与上位法不抵触”为原则,而对于设区的市,是以列举的方式严格框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这种立法范围的有限开放,是一种“减缩”“收控”的考量,属于“管理性”立法。
在单一制下,法制一统,中央立法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地方性事务不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地方立法的调整范围、调整对象、规制手段受到中央立法的严格约束限制,重要的许可、处罚和强制之设定权完全收归中央。1.处罚的种类只允许法律、行政法规创设,地方性法规不得染指;2.不断限缩处罚、许可、强制措施的设定权,留给地方性法规只有有限的处罚,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3.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才允许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
从程序上讲,采取批准、备案与说明义务等措施,要报送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合法性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才能批准生效。
因此,《立法法》虽然打开了地方立法的大门,但并没有界定清中央与地方立法的各自边际,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划分,只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义,在确保中央权威和法制统一的大前提、大背景下,在“不抵触”的严格尺度下,地方立法若想有所“突围”“创新”,是要受到严格的合法性审查,如想“有所作为”,增设制度、增加手段,只要与上位法“不一致”,就有可能是“放水”,是“抵触”,引发争议,质疑,警觉,就会成为风险,要问责。因此,表面上看,地方立法很热闹,实质是越来越趋于慎重、严格和保守,发展空间受到严格限制。
二、可用“办法”不多
在立法实践中,上位法的规定和现实存在明显差异,一些上位法规定的处罚、许可、强制,对于实际的管理工作来说是不够用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经常面临着立法空白、模糊抽象、不可操作的困扰,面临着上位法无法满足执法需求的情形,面临着法律依据不健全、执法手段不够用、合法行政无保障的困境,存在处罚不够用、许可空间小、强制手段少的状况。
1.行政处罚权限不够用。《行政处罚法》无法满足社会复杂多样的处罚需求,很多地方出现了创设新的处罚种类、扩大行政处罚幅度、新增行政罚则等情形。如,创设信用处罚,将违反法律法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纳入社会征信系统中,剥夺违法者获得各种权益的资格等;比如,某些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太低,为了严厉打击该种违法行为,一些地方提升了罚款幅度,超过法定的处罚额度;再如,上位法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执行落实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增设了罚则。
2.行政许可空间不够大。部分地方性法规在扩大或者缩小许可范围、增加或者减少许可条件、改变禁止性规定等方面,设定了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许可条件。
3.行政强制手段不够使。《行政强制法》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有五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有六种。然而,一些地方性法规超出了查封和扣押这两种强制措施。如“封堵排污口”,又如“销毁”“扣留”,这些都不属于《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强制手段,存在着合法性问题。
如此,地方立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要么,不顾客观实际,盲目照抄、复制,大量雷同,没有特色,充斥着大量指导性、倡导性、宣言性的条款,没有“牙齿”,没有“法味”,立法的意义和价值有限;要么,作出某些超越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突围冒险,出现了“下位法超越上位法”的抵触现象,在全国人大对云南环境保护条例的专项清理中,在现行有效的175件单行条例中,120件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其中有56件就与上位法的规定不相符合,85%的处罚幅度与国家不一致。如果一旦启动合法性审查,完全有可能被视为抵触,不合法,面临着无效的后果。造成这种“不合法”,还不能单纯地指责是地方立法人员的素质问题,不懂法的问题,而是这种做法,往往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更能满足现实的社会治理,更能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三、地方立法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九大以来,强调依法立法,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机械、僵化地复制、抄袭上位法,不行,越权、超越、创新,也不行。如何解决避免“立法短路”“法规打架”,如何为地方治理腾挪足够的立法空间,提几点不成熟想法。
(一)满足地方治理诉求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国家立法供给不足,需要地方立法予以细化、补充、落地,地方立法的闸门一经打开,立法需求呈不断高涨的态势,应给以必要的引导、鼓励或“试错”。立法无所作为,立法的价值大打折扣,地方立法权来自中央的“委托、授权和安排”,应通过授权方式,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
1.对于先行立法。先行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不存在上位法,从理论上说,应当具有完整的立法权,鼓励地方探索、创新。当然,在立法实践中,完整的、纯属地方事务的专属立法权极为少见,一旦着手立法,总会在某些具体内容上碰到上位法,因此,创新也不能任意妄为,不能违背上位法的精神和原则。
2.对于执行性立法,应当尊重上位法的立法规定,不能进行立法突破,当然,在能够实现上位法目的,确保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放权,允许地方有因地制宜的机变,由地方性法规来权衡具体的度与量,给予地方性法规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既充分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又能有效实现社会治理,允许地方立法增加违法行为并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调整处罚幅度,补充其他手段。
3.对于上位法规定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但没有具体的法律责任,没有设定违法行为及处罚的,不能放任或虚置,地方立法可以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予以补充完善。
4.在上位法规定之外的,地方立法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补充规定必要的、但有助于实现上位法目的的相关具体制度和要求,包括规定相应的违法行为及处理。对于上位法规定的各地必须严格执行的下限或底线的最低标准允许地方立法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上调处罚标准,以更好地推动社会的法治治理效果。
(二)留出必要空间
从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看,“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是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得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加大“回应型法”的构建力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性长期存在,上位法应该充分考虑这种现实,为下位法处理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事务提供立法空间,为地方立法留有余地。
从立法实践来看,国家层面的立法,由于开会次数和会议时间有限,效率慢,需要地方立法规制的事项又非常具体、急迫、重要,尤其对于设区的市一级立法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完全“等靠”上位法,“依据”上位法,不现实,也需“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
当然,法律是统一的、一致的、平等的规范,不能片面强调它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崇尚“地方唯一”,不能过分追求所谓的“首创”“原创”或“独创”,不能刻意去寻找“空白点”“差异点”或“创新点”,这会影响和削弱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纷争。为此,地方立法也必须保持必要的谦抑和服从,尊重并依据上位法,落实“越权无效”的法治理念,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立法冲突。
立法终究是要解决问题的,所谓“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不能因为害怕合法性审查的追责,不能因为绕开对重大争议问题带来的困扰,就放弃了必要的探索,如此,立法是安全了,但不管用。在判断下位法与上位法规定是否不一致的情形时,不应该刻意追求与上位法在文字上是否完全保持一致,而是要理性地分析判断地方立法是否给公民增加了实质上的负担和义务,是否存在“放水”,不能仅仅因为形式上规定的不一致,就武断地认为地方立法与上位法之间存在立法冲突。
地方立法应该充分行使地方立法权限,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地方特色,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事务,与时俱进,尽最大可能克服立法的滞后性和僵硬性,防止机械僵化适用法条,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下及时回应现实执法需求,应该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公众号
公众号
 小程序
小程序
 微信咨询
微信咨询